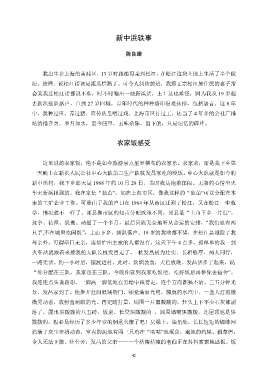Page 43 - 知青记忆.html
P. 43
新中浜轶事
陈良雄
我出生在上海的黄浦区,13 岁时跟随母亲到松江,在松江这块土地上生活了半个世
纪。按理,说松江话该是滚瓜烂熟了。可令人纠结的是,我那正宗松江原住民的妻子常
会笑我连松江话都说不准,时不时嘣出一些新浜话,土!这也难怪,因为我从 19 岁起
去新浜插队落户,直到 27 岁回城,青年时代的种种烙印很难抹掉,包括语言。这 8 年
中,我种过田,养过猪,宣传队里唱过戏,上海市区打过工,还当了 4 年多的公社广播
站的播音员。岁月如水,至今回望,五味杂陈。留下的,只是记忆的碎片。
农家饭感受
这里说的农家饭,绝不是如今旅游景点星罗棋布的农家乐、农家菜,而是我下乡第
一天晚上在新浜人民公社中心大队第三生产队杭发昌家吃的晚饭。中心大队就是如今的
新中浜村,我下乡那天是 1968 年的 10 月 28 日,当时我是抱着郁闷、无奈的心情坐火
车去新浜报到的。我在家是“独苗”,如在上海市区,像我这样的“独苗”可以分配在本
市的工矿企业工作。可是由于我的户口在 1964 年从市区迁到了松江,又在松江一中就
学,情况就不一样了。郊县和市区的知青分配政策不同,郊县是“上山下乡一片红”。
抗争、彷徨、犹豫、动摇了一个多月,最后只能无奈地听从命运的安排,“我们也有两
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上山下乡、插队落户。19 岁的我啥都不懂,在松江县城除了我
母亲外,可谓举目无亲,连帮忙出主意的人都没有。这天下午 4 点多,孤单单的我一到
火车站就跟着来接我的大队长杭发昌走了。 杭发昌极为壮实,长相憨厚,两人同行,
一路无话。约一小时后,摆渡进村。此时,炊烟袅袅,天色放晚。发昌话多了起来,说:
“你分配在三队,我家也在三队,今晚你就到我家吃饭吧,吃好饭后再带你去宿舍”。
我连连点头说谢谢,一脚高一脚低地在黑暗中跟着走,连个方向都搞不清。三五分钟光
景,发昌家到了。他推开灶间低矮的门,顿觉满目光明,朦胧的水汽中,一盏大灯泡微
微晃动着,放射出剌眼的光。再定睛打量,周围一片黑黢黢的,灶头上下不少石灰都剥
落了,露出黑黢黢的八五砖,饭桌、长凳黑黢黢的 ,四周墙壁黑黢黢,连屋顶也是黑
黢黢的,想必是经历了多少年岁的烟熏火燎了吧!房梁上,墙角处,长长短短的蜘蛛网
沾满了灰尘在拂动着,室内的泥地有两三只鸡在“咕咕”地啄食,遍地的鸡屎、稻草屑,
令人无法下脚。灶台旁,发昌的父亲——一个枯瘦枯瘦的老伯正在抖抖索索地盛饭。饭
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