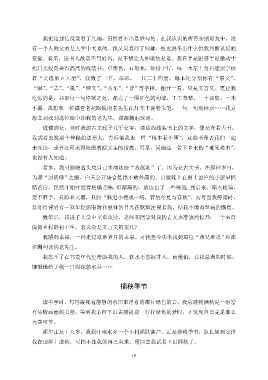Page 11 - 知青记忆.html
P. 11
我把这封信反复看了几遍,仍然看不出是谁写的。在我认识的所有亲朋好友中,没
有一个人的父亲是大学中文系的。我又反复问了阿雄,他也说不出什么供我判断认识的
依据。看来,送书人故意不写姓名,是不想让人知道他是谁。我在半是困惑半是激动中
把目光投向叠得高高的线装书。草黄色,石刻本,竖排字行,每一本左上角白底黑字标
着“文选第××册”,我数了一下,乖乖,一共二十四册。每本还分别标有“祭文”、
“赋”、“志”、“箴”、“碑文”、“音乐”、“诗”等字样。翻开一看,尽是文言文。更让我
吃惊的是,书里每一句停顿之处,都点了一圈红色的句读,工工整整,二十四册,一本
不漏。我想象一位戴着老花眼镜的老先生在灯光下提着朱笔,一句一句地标点……我真
想立刻找到这位暗中助我的老先生,深深鞠躬致谢。
遗憾的是,当时我的古文底子几乎是零,读这些线装书上的文字,像是在看天书。
我试着去找那个神秘的送书人,告诉他我也一样“根本看不懂”,这些书是否我们一起
来攻读,或者还可求得他做教授父亲的指教。可是,问遍这一带下乡来的“难兄难弟”,
也没有人知道。
看来,我只能硬着头皮自己来啃这些“故纸堆”了。因为是古文书,在那种岁月,
为避“封资修”之嫌,白天公开场合是绝不敢外露的,只能晚上在糊上窗户的小屋里悄
悄苦读。虽然开始时觉得枯燥乏味;但渐渐的,就读出了一些味道;到后来,渐入佳境,
爱不释手,只盼着天黑,只盼“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而每当我静读时,
总觉得背后有一双年轻的眼睛和慈祥的目光在默默注视着我,使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数年后,我进了大学中文系攻读,老师和同学对我的古文水准感到惊异:一个来自
偏僻乡村的初中生,怎么会是文言文的宠儿?
我感到幸福,一种走过艰难岁月的幸福。可我至今尚未找到那位“难兄难弟”和那
位圈句读的老先生。
我忘不了在书荒年代里帮助我的人。饮水不忘掘井人,而他们,在我最渴的时候,
慷慨地给了我一口深深的水井……
插秧季节
读中学时,每每凝视着静静的水田里浮着的那片绿色的云,我总感到插秧是一份富
有诗情画意的美差。等到我亲自下田去捕捉那一行行绿色的梦时,才发现自己竟是那么
天真可笑。
那年正是十八岁,我到江南水乡一个小村插队落户。正是插秧季节,队长原想安排
我在田岸上送秧,可挡不住我的再三央求,便同意我试着下田插秧了。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