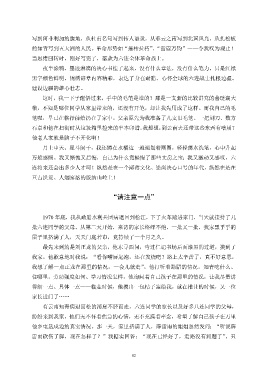Page 83 - 知青记忆.html
P. 83
写到阿非利加的腹地,从杜甫名句写到伟人语录,从彩云之南写到北国风光,从扎松板
的知青写到五大洲的人民。革命形势如“摧枯拉朽”、“雷霆万钧”——令我叹为观止!
当思绪回转时,刚好写完了,落款为六连全体革命战士。
夜半涂鸦、墨迹淋漓的决心书挂了起来,没有什么章法,没有什么笔力,只是红纸
黑字颜色鲜明,锦绣辞章内容精彩,表达了身在勐腊、心怀全球的六连战士扎根边疆、
建设边疆的雄心壮志。
这时,我一下子醒悟过来,手中的毛笔是谁的?那是一支新的比较讲究的善琏湖大
楷,不知是哪位同学从家里带来的,还没有开笔,却让我先用成了这样。而我自己的毛
笔呢,早已在临行前给扔在了家中。父亲原先为我准备了几支旧毛笔、一把刻刀、数方
石章和他在扫街时从垃圾箱里捡来的半本印谱。我想想,到云南去还带这些东西有啥用?
他老人家就是脑子不开化啊!
月上中天、星斗阑干,我还蹲在水桶边一遍遍划着圈圈,轻轻荡水洗笔,心中升起
万般感慨。我又惭愧又后悔,自己为什么竟轻慢了那些文房之宝;我又激动又感叹,六
连将来还会出多少人才呵!纵然是在一个鄙薄文化、崇尚决心口号的年代,纵然在是在
亘古洪荒、人烟寥落的版纳山岭上!
“请注意一点”
1970 年底,我从勐腊水利兵团病退回到松江,下了火车踏进家门,当天就接待了几
批六连同学的父母。从第二天开始,来访的家长络绎不绝,一批又一批,我家黑乎乎的
屋子里挤满了人,天天门庭若市,竟持续了一个月之久。
最先来到的是刘正龙的父亲,他东寻西问,弯过仁记书场后面漆黑的过道,摸到了
我家。他歉意地对我说:“看你嘴唇起泡,还在发烧吧?路上太辛苦了,真不好意思,
我想了解一点正龙在那里的情况,一会儿就走”。他打听着勐腊的情况,知青吃什么、
住哪里,劳动强度如何、学习情况怎样,他询问着自己孩子在那里的情况,让我尽量讲
得细一点、具体一点——临走时候,他摸出一包桔子塞给我,就在推让的时候,又一位
家长进门了……
有云南知青病退回松的消息不胫而走,六连同学的家长以及好多八连同学的父母,
纷纷来到我家,他们无不怀着焦急的心情,无不充满着牵念,希望了解自己孩子在万里
他乡屯垦戍边的真实情况。那一天,家里挤满了人,薛雷雨的姐姐忽然发问:“听说薛
雷雨砍伤了脚,现在怎样了?”我据实回答:“现在已经好了,走路没有问题了”。只
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