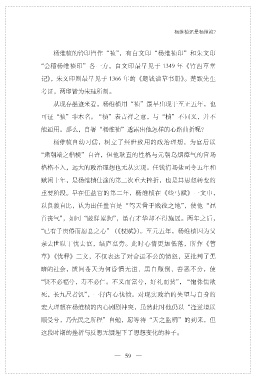Page 63 - “三高士”与松江(内页)
P. 63
杨维桢还是杨维祯?
杨维桢的钤印皆作 “祯”, 有白文印 “杨维祯印” 和朱文印
“会稽杨维祯印” 各一方。 白文印最早见于1349 年 《竹西草堂
记》, 朱文印则最早见于1366年的 《题钱谱草书册》。 楚默先生
考证, 两印皆为朱珪所刻。
从现存墨迹来看, 杨维桢用 “祯” 最早出现于至正五年, 也
可证 “祯” 非本名。 “祯” 表吉祥之意, 与 “桢” 不同义, 并不
能通用。 那么, 自署 “杨维祯” 透露出他怎样的心路曲折呢?
杨维桢自幼习儒, 树立了经世致用的政治理想, 为官后以
“肃朝端之楷模” 自许, 但他耿直的性格与元朝乌烟瘴气的官场
格格不入, 远大的政治理想也无从实现。 任钱清场盐司令五年和
赋闲十年, 是杨维桢仕途的第二次重大挫折, 也是其思想转变的
重要阶段。 早在任盐官的第二年, 杨维桢在 《些马赋》 一文中,
以良骏自比, 认为出任盐官是 “驾天骨于贱役之地”, 使他 “屈
首丧气”, 如同 “跛牂累狗”, 虽有才华却不得施展。 两年之后,
“已有子贡倦而愿息之心” (《杖赋》)。 至元五年, 杨维桢因为父
亲去世以丁忧去官, 结庐墓旁。 此时心情更加低落, 所作 《蓍
草》 《忧释》 二文, 不仅表达了对命运不公的愤怒, 更批判了黑
暗的社会, 质问苍天为何昏懵无道、 黑白颠倒、 善恶不分, 使
“贤不必福兮, 寿不必仁。 不义而富兮, 好礼而贫”, “饱侏儒欲
死, 长九尺者饥”, 一抒内心忧愤。 对现实政治的失望与自身的
宏大理想在杨维桢的内心剧烈冲突, 虽然此时他仍以 “逢逆境以
顺受兮, 乃先民之所程” 自勉, 愿等待 “天之监明” 的到来, 但
这段时期的挫折与反思无疑埋下了思想变化的种子。
— 9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