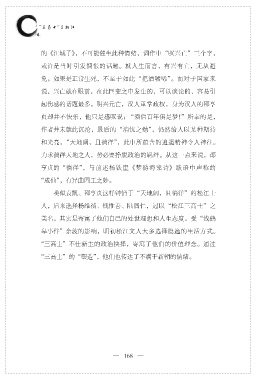Page 172 - “三高士”与松江(内页)
P. 172
“三高士”与松江
的 《江城子》, 不可能催生此种情绪, 词作中 “叹兴亡” 三个字,
或许是当时引发惆怅的话题。 就人生而言, 有兴有亡, 无从避
免。 如果是正常生死, 不至于如此 “把酒嘘唏”。 而对于国家来
说, 兴亡就在眼前, 在此巨变之中发生的, 可以谈论的、 容易引
起伤感的话题最多。 明兴元亡, 汉人重掌政权, 身为汉人的邵亨
贞却并不快乐, 他只是感叹说: “须信百年俱是梦!” 所幸的是,
作者并未就此沉沦, 最后的 “消忧之勉”, 仍然给人以某种期待
和光亮, “天地阔, 且徜徉”, 此中所蕴含的逍遥精神令人神往。
力求徜徉天地之人, 势必要挣脱政治的羁绊。 从这一点来说, 邵
亨贞的 “徜徉”, 与前述杨铁崖 《梦游海棠诗》 跋语中声称的
“成仙”, 有异曲同工之妙。
类似袁凯、 邵亨贞这样钟情于 “天地阔, 且徜徉” 的松江士
人, 后来选择杨维祯、 钱惟善、 陆居仁, 冠以 “松江三高士” 之
美名, 其实是寄寓了他们自己的处世理想和人生态度。 受 “钱鹤
皋事件” 余波的影响, 明初松江文人大多选择隐逸的生活方式。
“三高士” 不仕新主的政治抉择, 寄寓了他们的价值理念。 通过
“三高士” 的 “塑造”, 他们也传达了不满于新朝的情绪。
— 8 6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