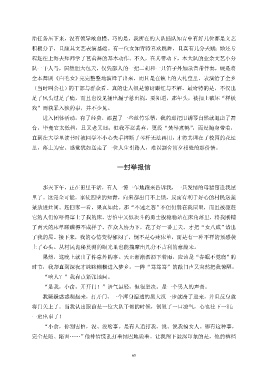Page 66 - 知青记忆.html
P. 66
治任务压下来,没有领导敢怠慢。巧的是,我所在的大队插队知青中有好几位都是文艺
积极分子,且颇具文艺表演基础。有一位女知青特喜欢跳舞,且真有几分天赋;她还专
程赶往上海去拜师学了芭蕾舞的基本动作。不久,在其带动下,本大队的业余文艺小分
队一干人马,居然胆大包天,仅凭鄙人的一把二胡和一只笛子外加录音带伴奏,硬是将
全本舞剧《白毛女》完完整整地演绎了出来,而且是在镇上的大礼堂里,表演给了全乡
(当时叫公社)的干部与群众看。真的让人很是惊讶眼红与不解。最奇特的是,不仅出
足了风头过足了瘾,而且也没见捅出漏子惹出祸。要知道,那年头,被扣上破坏“样板
戏”而获罪入狱的事,并不少见。
进入团体活动,有了经费,添置了一些丝竹乐器,我的那把旧胡琴自然就退出了舞
台,毕竟它太低档,且又老又旧;但我不忍丢弃,更没“焚琴煮鹤”,而是随身带着,
直到在大学里读书时被同学不小心失手摔断了琴杆无法再用,才将其埋在了校园的花坛
里,落土为安。感觉犹如送走了一位人生引路人,难以割舍朝夕相处的那份情。
一封举报信
那天下午,正在田里干活,有人一惊一乍地跑来告诉我,一只发情的母猪窜进我屋
里了。这完全可能。家徒四壁的知青,向来都出门不上锁,反而有利于好心的村民送蔬
菜放进灶间。赶回家一看,果真如此。那“不速之客”不但仍躲在我屋里,而且被驱赶
它的人们惊吓得窜上了我的床,害怕中又似决斗的勇士般稳稳站在床角落里,将我刚铺
了两天的床单蹂躏得不成样子。在众人协力下,花了好一番工夫,才把“女八戒”请出
了我的屋。接下来,我的心情变得郁闷了,倒不是心疼床单,而是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袭
上了心头。从村民诡秘莫测的眼光里也能揣摩出几分不吉利的意蕴来。
果然,这晚上就出了件意外的事。天正淅淅沥沥下着雨,应该是“春眠不觉晓”的
时节,我却直到深夜才眯眯糊糊进入梦乡,一阵“笃笃笃”的敲门声又突然把我惊醒。
“啥人?”我有点紧张地问。
“是我,小俞,开开门!”语气虽轻,但很坚决。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我疑疑惑惑爬起来,打开门,一个浑身湿透的黑大汉一步就跨了进来,并且反身就
将门关上了。当我认出眼前是一位大队干部的时候,倒吸了一口凉气,心也往下一沉:
一定出事了!
“小俞,你别害怕,没、没啥事。是有人追打我,说、说我搞女人。哪有这种事,
完全是陷、陷害……”他神情慌乱打着结巴地说着。让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他的裤裆
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