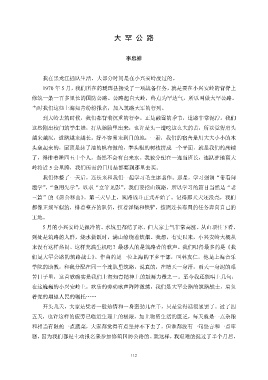Page 113 - 知青记忆.html
P. 113
大 罕 公 路
李忠祥
我在黑龙江插队生活,大部分时间是在小兴安岭度过的。
1970 年 5 月,我们所在的瑷珲县接受了一项战备任务,就是要在小兴安岭的背脊上
修筑一条一百多里长的国防公路。公路起自大岭,终点为罕达气,所以叫做大罕公路。
当时我们这些上海知青纷纷报名,加入筑路大军的行列。
到大岭去的时候,我们都背着沉重的行李。正是融雪的季节,道路非常泥泞。我们
这些刚出校门的学生娃,打从娘胎里出来,也许是头一遭吃这么大的苦,所以觉得肩头
越来越沉,道路越来越长。好不容易来到目的地,一看,我们的宿舍是用大大小小的木
头垒起来的,屋顶是抹了油的帆布做的,拳头粗的树枝拼成一个平面,就是我们的床铺
了,得排着睡四五十个人。当然不会有自来水。我被分配在一连当班长,连队驻地离大
岭将近 5 公里路,我们所需的日用品都要到那里去买。
我们休整了一天后,连长来和我们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那是,学习强调“带着问
题学”,“急用先学”,以求“立竿见影”。我们要挖山筑路,所以学习的篇目当然是“老
三篇”的《愚公移山》。第三天早上,筑路战斗正式开始了。记得那天天还没亮,我们
都像正规军似的,排着整齐的队伍,扛着洋镐和铁铲,按照连长布置的任务奔向自己的
工地。
5 月的小兴安岭是很冷的。水坑里都结了冰,但大家士气非常高涨。从山顶往下看,
到处是筑路的人群,烧水做饭时,满山缭绕着炊烟。我想,有史以来,小兴安岭大概从
来没有这样热闹、这样充满生机吧?最感人的是筑路者的歌声。我们唱得最多的是《我
们是大罕公路的筑路战士》。作曲的是一位上海的下乡干部,叫林友仁,他是上海音乐
学院的助教,和我分配在同一个连队里筑路。说真的,在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的艰
苦日子里,这首歌确实是我们上海知青精神上的鼓舞力量之一。至今我还能唱上几句:
在这巍巍的小兴安岭上,欢乐的劳动歌声阵阵激荡,我们是大罕公路的筑路战士,肩负
着党的期望人民的嘱托……
开头几天,大家是凭着一股热情和一身蛮劲儿在干,只是觉得活很累罢了。过了四
五天,也许这样的疲劳已临近生理上的极限,加上物资生活的匮乏,每天就是一点杂粮
和相当有限的一点蔬菜,大家都觉得有点坚持不下去了,但谁都没有一句怨言和一点牢
骚,因为我们都是主动报名来参加修筑国防公路的。就这样,我艰难的挺过了半个月后,
112